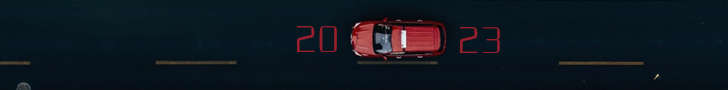高晓松说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跟着大家随波逐流的人,同时还不特别高看自己。但他大概是随波逐流的人中“运气”最好的一个,从校园民谣旗手到互联网大潮的一份子,从拍摄大荧幕电影到“小屏幕”的脱口秀,他总能取得成功并且引起关注。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诗词歌赋一通背,写诗赋词信手拈来。和高晓松对话需要随时集中注意力,因为重要的信息总在他的嬉笑之间。果不其然有两个高晓松,需要由你自己去寻找。
作者/冯寅杰 编辑/张欢(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
一张脸,5亿次浏览量
《南方人物周刊》:《晓说》这档视频脱口秀最初的策划思路是如何形成的?
高晓松:最早是吃饭,开始我还没去,约了三回才去,我经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死拉活拽。优酷当时也不知道要干嘛,就想跟你合作。合作什么呢?就说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我说这多麻烦啊,还得再弄一棚子,排练半天,嘉宾这那的,我说要弄一个最简单的,就我一个人说话。其实大家都没觉得这个事最后能怎么样,不知道节目能不能卖。结果就一个人(鲁浪)跑我们家去了,就录了,然后就成这样了。我是属于老派的,电影、唱片最好,一定要印刷出来。我们唱片公司改名音乐公司我还伤心了很久,唱片公司多好听,音乐公司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改了。
《南方人物周刊》:当初做《晓说》的时候,有没有预想到能那么火爆、成功?
高晓松:没有,我做什么都没有预想到会成功,我也没想到《同桌的你》票房4.8亿。我想8千万,后来前面多一个4,这个没想到。我做音乐也没想到会有人喜欢,录完了第一张,出棚的时候我还跟老狼说,肯定没人喜欢,你丫唱得也不行,我怎么听怎么觉得不行,吉他弹得也不好,歌唱得也不好。可是大家都说好,我就觉得都挺好的,我是一个很容易跟着大家随波逐流的人,不是那种特别高看自己的人。这个我更没想到,这么一张脸,有5亿次浏览量。我天,5亿次看我这张脸,我真没想到。再乘以分钟的话更可怕,150多亿分钟,夜里会做噩梦吧。
《南方人物周刊》:你从优酷“转会”到爱奇艺,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古永锵怎么看待这件事?
高晓松:互联网是个跳槽很频繁的行业,连高管、CEO都跳槽,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让我挺高兴的,不像20年前,怎么回事我把你捧红了,你他妈跑了。现在大家也都挺习惯的。张艺谋导演签了乐视,大家也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常嘛,商业社会。但是我呢,尽量做到跟大家都保持着,我和Victor Koo(优土集团总裁古永锵的英文名)现在也保持了很好的友谊。他是一个很不爱交际的人,几乎晚上不出来。当然我最后签约的时候是最先跟Victor Koo(古永锵)说的,我说我已经签了别人了,但是没关系,大家还都是朋友,OK,有空聚,几位大佬回得都特好。那天是在双秀园的茶馆里,我没有邪乎,深情版的。他问我觉得和大马(马云)合作好还是小马(马化腾)合作好。Victor Koo(古永锵)也是《晓说》迷,期期都看。
《南方人物周刊》:转会爱奇艺是否因为有些东西是优酷没法给予的?
高晓松:其实我觉得爱奇艺最重要的是风格,跟我谈事的风格,他们比较了解我。我不会谈生意,也不会算帐。有人给我一套复杂极了的分账方法,这啊那啊,我就看不懂。我并没有想要很多东西,我也没想要特别多的钱,我也没想要特别火的节目。爱奇艺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家一块儿玩玩,我觉得挺有意思,大家能聚一块这样。
《南方人物周刊》:此前有人专门为《晓说》估过值吗?
高晓松:优酷自己内部肯定估过。爱奇艺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其实也就是做这一个节目,。因为《晓说》有一点好,它囊括了一切。比如我有一个笑话,就把笑话讲《晓说》里;我想唱歌了,在《晓说》里抱把琴唱不就完了嘛;我想做军事排行榜,我也把它说在这里面。所以我就说,最好只干这一件事。换句话说叫徒手卖艺的事,都扔在这里面就完了,其他几件事都是摄影机、吉他和笔。《晓松奇谈》也没规定我要说什么,从来都没有限制。
《南方人物周刊》:从《晓说》到《晓松奇谈》,从优酷到爱奇艺,你的分成机制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高晓松:我基本上都不管这些事,我也懒得监督人家,还天天看你挣了多少钱。其实也没外界传得那么邪乎,没那么多钱,说实在的。包括电影我也是,最后我就看票房,人家跟我说多少就是多少了,书人家跟我说印了几本,我从来没到出版社查单子,我特随意。
想得浅,说得深,容易被逮到
《南方人物周刊》:脱口秀类型的节目似乎更适合生存于互联网时代?
高晓松:对,因为我自己没有证据倾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限制。比如说柴可夫斯基,我说他是同性恋,要不然说什么呢,哼歌?柴可夫斯基的一生都和他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包括他的作品,他最终为什么会死,都和他的身份有关系,今天的人都认同这个。当然,中国有中国不能说的,美国有美国不能说的,我就是卖艺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位《晓松奇谈》和《晓说》?
高晓松:我自己也在摸索,美国并没有这种类型的节目。主要原因是美国人不喜欢历史,美国中学历史及格率才12%,历史考试就拿地球仪让你指美国在哪,一般都是这样。美国学生及格率最高、成绩最好的商科,然后经济,最差的就是历史。
《晓松奇谈》基本上会延续之前《晓说》的思路,谁都没想有什么大变化。所以我先讲世界杯,讲六期,其实是讲32国的历史、恩怨。然后我就说,他们讲杯,我讲世界,加起来就是世界杯,因为我讲球讲不过别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没有关注其他类似的视频脱口秀节目,例如罗振宇的《罗辑思维》?
高晓松:我看过他的一点儿,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没敢看。我怕我从人家那偷观点,会不由自主。我说的时候我没稿,我也不知道从哪就进入到我脑子里了,说得特跳跃。基本上我的准备是先直接在饭桌上跟人聊,人家听完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才讲。人家说你什么都懂,其实不是,我只说我懂的,没吃过的饭不聊,没去过的地儿不说。
《南方人物周刊》:做节目是知识输出,那你知识储备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高晓松:看书。走到哪,就找知识分子聊聊天。在新西兰,我去找维大的校长聊,特别有意思,他还知道郑和。每一期节目下面的评论都有方家,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一看这下面有特懂的人在那说,这个补充其实也相当重要,所以我在录《晓说》的最后一期还感谢这些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反正都是一些方家。
《晓说》讲的主要是识,知识够不够不重要,见识够了很重要。同样的事你都知道,但是我把它联系起来了,这是我的节目最好的地方。其实我没有猛料,我说的是这几件事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大家都知道哥伦布,我讲的是哥伦布为美洲带去了马、牛、羊,怎么改造了大陆,带出了玉米、白薯,全世界的人口因此暴涨。我这样讲,这个角度就挺有意思。主要是讲识,而不是讲知,知的部分上学就行了。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知识的结构和能力是什么时候开始奠定的?
高晓松: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我们家吃饭最爱聊的事就是讲国外。从小训练记国旗、背首都,甚至我自己闲着没事,都把各国的煤产量、钢产量背了一遍,慢慢形成了习惯。我们家人最讨厌的就是胡说八道,因为科学家最讨厌的就是立论。
另外我在国外呆着。在美国有大量的(中国)看不到的中国的历史,包括我在美国买的那597封电报,就是1930年中原大战时期的,那些资料你在中国看不到。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我也去看了,而且看的人之多我都没想到。能看到的各方面资料极其之多。所以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这种比较愿意把事去深入地想。想的深,说的浅,比较容易。最难的是你想得浅,但说得深,就特别容易被人逮到。
谁都可以把梦想拿出来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最早一批参与互联网浪潮的精英,通过这些年来的经历和感悟,你如何看待当下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高晓松:我从2000年开始做搜狐的总监,然后做新浪的首席顾问,盛大的首席顾问,A8的总监到优酷这一系列,我跳槽最多。当年我第一次见张朝阳时我就说,你是物理系的,你不是做IT的,你是做I的,Information,就是做信息的,你不懂T,科技你不懂。那时候特简单,跟我聊的都不懂,期权之类的。后来张朝阳说那咱俩工资一样,我说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工资多少。中国人习惯拿历史当镜子,有人说看不懂这一轮科技大潮,所以总觉得这事成不了,结果一个一个成,而且成得特别大。当年搜狐上市的时候,我们被马云请到杭州去做西湖论剑。当时我们想马云凭什么请大家去西湖论剑,当时阿里巴巴很小很小,而新浪、网易都已经上市了,就觉得这个(阿里巴巴)模式肯定不行。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时代,谁都可以把梦想拿出来,不光是说,而且可以比划两下,做什么都可以。你怎么看一个学无线电(高晓松曾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的干这个事?
《南方人物周刊》:在美国,像Netflix这样的网站通过《纸牌屋》开始成为制作公司,而中国的视频网站会不会以视频脱口秀节目为模式,复制到美国去?
高晓松:Netflix只是一个发行商,华纳电影最早也是给人放电影的,然后去做制作。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多的发行商,就是Netflix,它可以做视频网站,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制作网站,它自己去制作了。
实际上,我说的制作不是制作我们这种节目。它应该是全产品线,电影、电视剧,甚至是大电视剧,就是美剧,就13集,短的是22集。我看现在大家也都开始走上这条路,这条路是必然趋势。因为当你手握现金的时候,你没事闲的要人家成品给你叫价,让你买,大视频网站手握这么多钱,有什么做不了的。
《南方人物周刊》:身处视频公司激烈加惨烈的争夺战当中,你自己最切身的感受是什么?
高晓松:我当然有感受,我这节目美国没有,因为美国特别严谨,全是写好的。我这次在格莱美,那主持人四个写手,每首得奖的歌或唱片都写出五个,因为你不知道谁得奖了。这次我坐最前面,每个颁奖人说的话,题词器上都有,连“晚上好”都写上去了,所以那是个特严谨的事。坐那胡说八道的,在美国都没有。全都有团队,都是事先写好的,这是美国的方式。在美国没有这种行业(视频网站),在美国没有乱卖版权的公司,谁出钱要都把索尼和华纳放一块去了,这在美国都不可想象。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的大型视频网站都是靠起初版权混乱的时候起家的,但最终集聚起大量资金以后,都要回头重走美国的老路,成为一个大型Studio。现在的商业模式很成问题,现金最多的一方去买用现金少的那一方的产品,这个事不是很怪吗?应该是现金最多的一方做生产方,因为生产最需要现金,最需要积累大量的剧本,积累大量的戏,去生产。现金少的一方,在美国比如说院线等等,是去做发行,去做下游,或者去做上游经纪公司。所以我跟几位大佬也都谈过,觉得现在就应该在大型的视频网站里普及好莱坞大师的生产、管理、金融以及保险办法等等。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硅谷与好莱坞文化的区别,互联网对传统行业那种摧毁式的创新?
高晓松:没有摧毁,我觉得挺好的。还是那句话,谁掌握最大的资金在手里,谁就掌握最大的资源在手里。互联网现在像电一样代替一切。
但硅谷应该算加州人民最骄傲的事,北边的硅谷,南边有好莱坞。我之前在优酷,包括在爱奇艺,发现基本上视频网站的海归都是从北加州回去的,好莱坞的海归还没有,因为华人在好莱坞还没有干起来的。硅谷有大量的华人,清华有一万多同学在硅谷,基本上回国的海归都是从硅谷回国。别看这两个地方开车就5个钟头,这俩地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所以从硅谷回来的人,说要重新做好莱坞的事,都会觉得有点不熟悉,那是另一套东西。现在好得多了,慢慢从好莱坞来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这几年学电影、学艺术的多起来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和这拨互联网领域的箐英领袖的关系怎么样,怎么看他们?
高晓松:互联网这拨人都有一些各自特别神奇的地方。这些人都有点水浒里三十六、七十二星宿的劲,都挺怪的。比如张朝阳其实是很喜欢娱乐业的人,他在MIT(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企图在好莱坞当演员。龚宇是我的校友,Victor Koo(古永锵)是我搜狐的同事。他们身上展现的智慧不是通常的知识分子的智慧,也不是通常意义的商人的智慧。
互联网这些人年纪比我还小,他们那种看世界的伶俐的角度,以及对人的那种能量化的能力,我都觉得特别神奇。他们做人的生意,最后做到十亿人的手机里全是他们的东西。包括我的话语权实际上也是他们给的,如果没有他们,就像木新老师当年在纽约一样,每周给大家讲文学史,要么在谁家,要么在一个饭馆里,讲了五年,但只是给十几个人讲。因为他们的原因,我才能有话语权坐在这给千百万人讲,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木新老师能有今天,也会有无数人看。
好歌大家都想要,烂歌给谁都不要
《南方人物周刊》:视频脱口秀占据你多少精力,有没有计算过自己的身价?
高晓松:一年占26个下午,一下午录两期,26个下午就录完了,相当于五分之一部电影。因为电影拍就要拍三个月,然后前面准备,后面准备。收入反正没有外面传得那么吓人。电影现在我不知道身价,因为弄出一个4 .8亿的电影。你的价钱也不是你定的,就像一个歌手走秀要500万一场,结果就给50,所以你没办法自己定身价。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将来类似《晓松奇谈》这样的节目会不会被视频网站批量生产,并形成某种标准?
高晓松:个人创作的东西都没办法批量。电影可以批量,那是集体创作。选秀节目也可以批量做,你只要做出新的,比如椅子转了,掉房顶上了,反着听都行。但是个人创作的东西,比如说音乐、绘画都不能批量生产。我举个例子,美国号称自己的娱乐业有多强大,你再做个迈克尔·杰克逊出来,那多挣钱啊,他也做不了。港台唱片业再来两个周杰伦,再来两个方文山也行了,但是没有啊,个人创作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所有的,写诗、绘画,等等这都没有办法复制。只有工业化的东西可以复制,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可以复制,爸爸可以去这,爸爸也可以去那。
我还是像老艺人的那一套,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开始说得磕磕巴巴,脑子经常短路。嘴一瓢还老说错,第一期就说错了,哪个电影哪年得了金马奖,就说错了。我以前上台,为了想我下一句说什么,都看不见观众。现在我能看清楚观众的反应了,就更有节奏一些,他来劲了就可以抖包袱了。老狼、朴树刚上台唱歌那会儿全走调,压根就没唱在调上,现在人家不但能唱,还能跟观众互动,表演性的东西。我以前特别佩服郭德纲、周立波他们,他们能控制住观众的呼吸,知道什么时候包袱一砸,肯定响。以前我聊着聊着不知道哪去了,我的风格就是这样。这两年自己慢慢也瞎琢磨出来,慢慢有点意思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未来内容的生产模式,中国在这一点上是否会与美国趋同?
高晓松:我特别少回国,回来要参与的事情也越来越少。现在回来主要就是恒大音乐,但它也会有更多的业务在美国。今天的市场已经容不下这么多钱了,现在不是钱少,是东西少,所以要向外扩张,要国际化。美国也完全敞开了要和你合作,到处都是中国人,全是中国公司收购人家企业,收购不了企业的把人家的CEO挖出来。未来整个行业,不管是电影、音乐、脱口秀各个方面,未来最典型的合作方式应该是中国的钱加上美国的高端团队。再过一段时间连美国团队都不用,都能自己来。创作上会有更多这样的人,两边都懂。
《南方人物周刊》:签约恒大音乐以后有什么变化吗?
高晓松:恒大能上市啊!所以包括宋柯当时卖烤鸭也是想的一个局,因为我们要收购很多家,恒大肯定不可能从头开始做,一定要收购几家公司才能做起来。你收购人家的时候,人家要开价,我就说咱们先给整个行业泼泼冷水。于是宋柯就到处说我要卖烤鸭去了,行业已死,然后行价就都下去了。
例如太合麦田,虽然我们已经不在那了,但是我们依然是创始人,我和宋柯。现在已经不是拼量的时代了,而是拼手里的优质版权。麦田手里有李宇春、朴树、田震、郑均,因为收购了红星等等一大批优秀版权,在我们行业叫钉子。你没这个钉子,永远成不了一个大品牌。我是钉子户,一扎,你把我拆了也没用,盖不起楼,因为你没有朴树,没有李宇春,没有许巍,没有郑均,没这几位的版权,你怎么开张啊?音乐是必须全有,你少一个也不行。因为上来听歌的人,人家想要十首歌,有俩你没有,人家还得再去另外一个音乐网站搜那俩歌。等于要三个界面同时开着才能把一个歌听完,这是不行的。音乐是靠list听,人家一听半个小时,所以人人都得有全版权才能经营。所以接下来唱片公司都值钱了,好歹有一个钉子在手里。
音乐行业的体量要比电影、电视大得多的多,因为听音乐的人是8亿人,音乐是呈千亿级的点击量在网站上。一年的整个产值至少是电影的十几倍。中国电影增长这么快,一年200多亿。中国移动光彩铃一年就340亿,一家光卖彩铃就比全国2万块银幕拼命放电影大得多。卡拉OK比电影院多得多,一个人在卡拉OK消费多少钱?一个人在电影院消费了多少钱?电影票加一个爆米花。所以音乐本身是一个体量比电影大得多的产业,营收至少是电影的很多倍。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和美国,因为国情的不同而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例如盗版,美国又是怎么解决的?
高晓松:版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中国的版权,这个事天天说,说了一辈子。我说其实是没有用的,我还是中国最大的音乐风云榜的主席,主席年年上去骂也没用。但现在好了,你盗版是盗的腾讯的版,阿里的版,360的版,那就没我事了,你们打去吧,那几位大佬能随便盗版吗?音乐行业以前又没钱又没能力,唯一的能力就是有俩老艺术家进中南海,发点牢骚,还就是有点摇滚乐队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能力。
当然美国也在下降,美国的下降是因为烂音乐没人听,导致原有虚高的下降。原来你凭什么赚那么多钱,是因为你拿了八首烂歌,配了两首好歌,卖给人家。其实我不客气地讲,原来的音乐产业产值有一半的是虚高的,是垃圾歌曲,配了好听的歌,挣来了黑心钱,已经对不起歌迷长达60多年了。港台唱片公司有严格规定,四首好听歌一定把两首放第二张,一定要配八首烂歌,因为好听的歌不容易拿到,拿到这两首别放在里面,有这两首就够卖了,而且好听的歌做着贵。磁带有B面,就找专门的B面写手写几个,然后就凑数了。所以音乐行业当年的暴利是有原罪的。互联网干的事就是,好歌可以给你钱,但是不能烂歌也找我要钱。所以音乐界,发牢骚的时候也想想当年,大家也别天天怨天尤人,你生产过多少烂歌,这些烂歌搭着好听的歌卖了多少钱,在每个人的磁带上,在碟子里?已经提前把该挣的钱挣了,现在就是受受苦,活该。公司应该都认识到这一点,减少产量,只唱好歌。好歌大家都想要,烂歌给谁都不要。
怀念的不是青春,而是你的荷尔蒙
《南方人物周刊》:你现在是中国最著名音乐制作人,同时又是词曲创作者、电影导演、作家,为什么每一波浪潮到来时你都能很好地赶上,并且做得都不错?
高晓松:对,我是命好,中国刚有唱片公司的时候正好我写了那些歌,我早写十年就不行了。每次别人问我为什么脸更大了,我都说馅饼砸的。我自己亲眼见过很多比我有才华的多的人,比我深厚得多的人。我在每件事上都见过很多怀才不遇的人,可能比我还好。所以就觉得我不就是命好吗?我现在在筹划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人总要报答一下,要不然老天爷哪天醒过来怎么弄错了,怎么都是你。只能多行善,做点让自己觉得心里平静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脱口秀节目之外,现在手头还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或亟待完成的?
高晓松:我现在特别想翻译小说,还在纽约做了一个音乐剧,这个是我特别高兴的。我买了严歌苓的《扶桑》,是我最喜欢的她的作品。电影版权她现在最火,但是音乐剧没人敢买。我买了在纽约想做成百老汇的戏,因为《扶桑》讲了旧金山的故事。这些事都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挺好,本来没4.8亿也不急,现在有了这个更不急了,我也拍过4亿多的电影,我着什么急。今以年来,我写了不少好听的歌。但我还是喜欢原来的方式,写一堆歌找一个人唱出来,是比较好的。
要说我什么都满足了,唯一的还剩最后一条,有时候午夜醒来把自己吓一跳,想想自己还不是博士。因为从小在这种家庭长大,这个压力特别大,你好歹得是一个博士。我一看我妹也去读了,所以午夜醒来,觉得是不是要去读一下。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不是最好的时代?
高晓松:对于创作者来说没有最好的时代,只有个人成长的历史。对于整个时代来说,每当科技迅速发展的时候都是文艺靠边站的时候,通常都是科技带领人们撞到这个墙上,人们疑惑了,文艺再上来。现在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时代,科技和文艺同时发达。通常是文艺特别强的时候科技是停滞的,最典型的就是神话时代,科技什么都没有,解释全世界的是靠神话。但科技会带领人们撞在一个墙上,比如说一战,钢铁大炮居然杀了那么多人,杀人效率如此之高。大家才醒悟过来,原来科技把我们带这儿来了。所以一战以后才有一个文艺的大高潮,才有毕加索、海明威等等,新的艺术全都出现了。而现在就是科技最昂扬前进的时候,比工业革命时代还要昂扬。文艺在这种时候都要靠边站。科技前进的时候,人类大规模地改善生活,就不绝望,也不去思考这些东西。互联网也一定会像以前所有的科技一样,会把人类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开始反思。这个反思的时代可能不会太远,到时候又会有大师出现。每次人家提这个观点的时候,我都反驳美国把英文都简化了,知识分子都气死了,英文单词拼得都不知道词根在哪里了。英国的歌词写得像诗一样美,美国人写歌词只会写Baby,baby,I love you。但是美国有硅谷,有好莱坞,所以我觉得那是少数精英的失落。互联网让一些知识分子觉得难过,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每当科技进步,知识分子都会难过。每一次科技大潮把人类卷到一个地方,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再把人类往回捞一捞。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说过赚钱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为什么?
高晓松:赚钱当然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性在逐级降低。你赚你的吃饭钱是最重要的,怕饿死,你赚一辆车的钱也挺重要,要不然你的生命都耗费在公共汽车里了。但我的(赚钱)热情直线下降,每天都有人跟我说,咱们干这个事能挣多少钱,挣那么钱干嘛。我现在也挺好,也不买房,我的车都是分期付款,每月付一点儿,三年以后还完了就行了,我从来没有全款买车。我就一个月花500美金,三年以后我再挑一个新车,再每月付你500美金。我没有特别大的花费。
《南方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青春岁月,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高晓松:每个人都怀念自己的青春,不管是今天陌陌上的还是过去乐队的年轻人,都怀念。因为你怀念的其实不是那个时候的乐队和这时候的陌陌,而是你的荷尔蒙。
 iNews新知科技 关注科技,自有新知
iNews新知科技 关注科技,自有新知